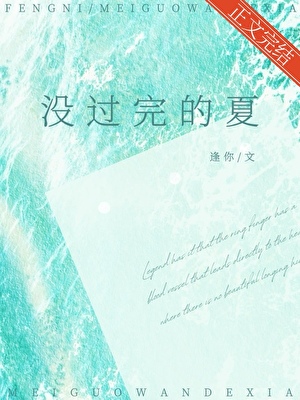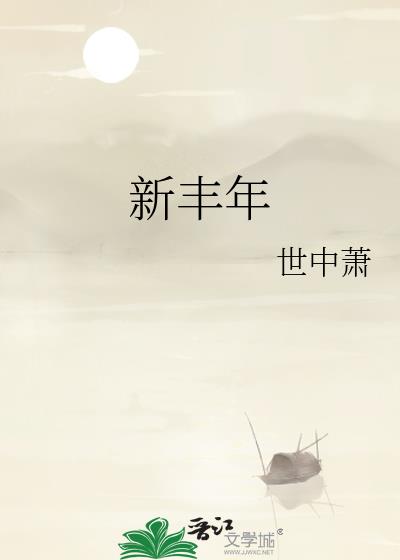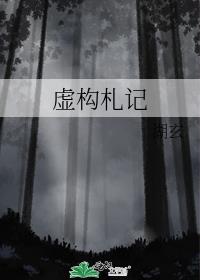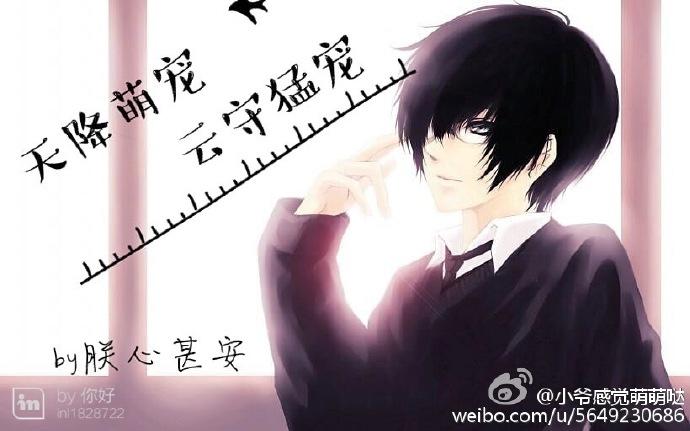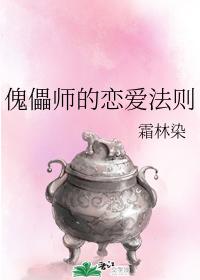新豐年 — 第 21 章
第二十一章
按理來說,周绮華教授不會什麽都和別人說,但偏偏這個夏垂君不一樣,為什麽呢?
“我嘛,和你們周教授是大學同學,我們在位于東亞的本州島的海島文史哲學院三學院就讀,畢業後到了位于夏威夷島的海島文史哲學院一學院就職。”夏垂君和他們講着這些事,但她的語氣就像是在說着一個遙遠的故事。桌面上的茶冒出氤氲的水汽,在蒸騰之下越飛越高,直到消失不見。
夏垂君把手放在水汽上,感到手上的溫熱後,又緩緩說:“後來嘛,我辭職了,她還接着幹,一直幹到寰球文明學院去了,挺好的……你知道我們在讀書的時候住的是六人寝,但是我們的序號是班裏的最後兩個,然後就是我們倆占了一個六人寝,讀書四年來我們都沒有吵過架,真的,我從來沒有碰到一個性格和我這麽相和的人,直到現在還保持固定聯系。當然,這得多虧方兄的老無人機,就靠那鐵疙瘩才讓連接了我們,不然我總是跑到那收不到信號的去接不到消息。”
方鎮節擺擺手表示謙虛,方康江岳便又接着向夏垂君問:“那您怎麽又不當教師呢?不然說不定您也能教我們這輩人多點知識呢。”
夏垂君的嘴角勾起一個看不穿的微笑,眼神盯在茶杯上,輕笑一下:“怎麽說呢,這是個很複雜的故事……不對,這個故事挺容易講的,簡單來說就是某個高官的無恥故事。”
方家這三個人都是一頭霧水,特別是穆定夫斯基這個向來眼神迷茫的人來說,更是有別樣的效果。
在這短短的幾秒鐘裏穆定夫斯基頭腦發暈,而方康江岳卻頭腦風暴了好幾個問題了:這個世界這麽小的嘛?我導師怎麽什麽人都認識?夏阿姨人生經歷是什麽樣的?我現在直接問她會不會不太禮貌?揭人傷疤不太好吧,我爸應該會打我吧?要不我去問周教授?啧,我好奇心怎麽這麽重……
夏垂君還是發話了:“這事也不是不能說,也算是給你們這些小輩長點見識,免得看錯了人。我在當民俗學副教授的時候要寫考核論文,一般來說自己必須是主筆人。我的最後一篇考核論文是有關浮世繪的文章,但你們也知道,有的資料是公司或者是個人管控和收藏的,想要看到是需要大筆資金的,那時候的市價是一分鐘三萬。而且想去看還要渠道,我就沒有什麽渠道,這個時候時任教授的某高官給我找了個收藏了浮世繪視頻的私人,一段視頻裏可能有幾百張手繪,片量巨大。我當然對這家夥感恩戴德,只是沒有想到這家夥也在考核期,通過校內關系直接在這篇論文上把名字加在我的前面。這一加不要緊,加了就要命,他直接成了主筆人。”
“那後來呢?”方鎮節也聽得入迷。
“這種事情我怎麽能忍?第一,這事關我的考核;第二,這人人品不行,他只能算個中間人,還想加名字?我當然找學校去說了,你們知道他後來說什麽‘我只是覺得有我的功勞,就找人加上去了,沒有想到不小心成了主筆人’。我還能說什麽?不久,他從學校辭職後,又通過關系從了政。”
穆定夫斯基幾乎是大叫一聲:“這簡直不可理喻!”
方康江岳被吓了一跳,夏垂君又接着說。
“不過我還是明白一個道理,做學問的,特別是民俗學,如果你不真誠的深入民俗文物的內裏,你永遠做不好這一門學問。所以我選擇了辭職,走遍世界各地去尋找民俗文化,就算現在世界上高樓林立,我做的事情格格不入,我也願意深入地下挖掘那些為人所不知。”
方父拍手叫好:“你這話說得真不錯。”這可能就是同為獨立文化工作者的惺惺相惜吧。方父又接着說道:“難怪你今天一來就我談什麽體制的問題……小方,你手上那塊機械表取下來給我。”
方康江岳“哎”了一聲,把表從袖子裏面掏出來,那是構造為蝴蝶扣的手表,通體是銀白色的,很多地方都有細小的磨損,證明了這塊表的飽經滄桑,表盤上做了波浪樣的紋理。作為一個古董,這塊表的三個指針還在不停工作。
方父接過這塊表,一手提着表帶,将其平整的鋪在手上,伸出手去給夏垂君展示。夏垂君從她民俗的角度看,這個款式經典得不能再經典了。
“你知道這塊表的第一任主人是誰嗎?”方鎮節對夏垂君露出一個微笑,“是覃聯道。”
“就……就是那位衆世黨第一位決策官?”方康江岳從來都覺得文物離自己很遙遠,就算是在家裏觸手可及,琥珀就是琥珀,花瓶就是花瓶,所謂可遠觀不可亵玩。但沒有想到寫在課本上偉人的表居然就戴在自己的手上,那人可是多少寰球文明學院學生的偶像呀!
“你說的那種人向來只是一小部分,是毒瘤般的存在。但是我們當代人的生活還是挺好的,這說明現在的體制還是沒有什麽問題嘛。”方鎮節攤開手。
夏垂君苦笑一下,也不知道是什麽意思。
“沒關系,我們不聊這個。來來來,我們來看這塊表,我一直想拆開看看,但我覺得這塊表應該和別的差不多,應該是偉人的光環讓我想拆吧……”
方父瞬間就将話題扯開了,兩個人又聊得火熱,獨留方康江岳和穆定夫斯基在風中淩亂,兩人只能默默離開。
兩人上樓的時候,方康江岳偏過頭問:“你有什麽愛好嗎?”
“啊?”
“一猜就是這反應,”方康江岳哭笑不得,“我們家樓上有間小書房,要不咱們去看書消磨一下時間。”
所謂“小書房”,其實在頂樓的閣樓上,簡直大得吓人,說是圖書館也不為過了,況且裏面有古今世界各地的藏書,可謂書海了。
陽光灑進閣樓,讓閣樓裏沒有那麽潮濕更好保存書籍。而陽光也讓視線明亮,讓讀書人的視線也剛剛好。
兩個人就坐在閣樓裏,每人捧了一本書,也不說話,他們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。
若是此時有個攝像師,拍上一張圖,他一定會驚嘆:有的時候不是自己的攝像技術有多麽高超,只是那一刻的光線,那一刻的時間,那一刻的人都剛剛好。